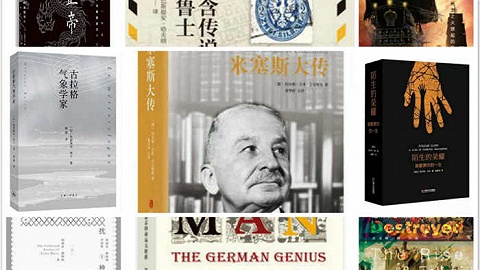“我们应该维护妓女职业选择的自由和权益,还是认为妓女是男权消费的受害者?”
“为什么男性总要被塑造成一个积极阳光的角色,而女性恰恰相反?是不是女人因为生理上的差距,因为少了一个性器官,就要做一个柔软的东西? ”
“女性如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争取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还是用女性逻辑去改造整个社会?”
围绕这些问题,上周末诗人翟永明、学者李剑、艺术家秦玉芬以及主持人王歌在北京歌德学院一场以女性为主题的沙龙上,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谈改善妓女的工作环境还有点奢侈
翟永明在沙龙开始前朗诵了自己的诗歌《雏妓》。2002年,她在新闻上看到一张中国雏妓的照片,得知这位12岁的女孩被拐骗从事妓女职业,100多天内“服务”了300多个男性。翟永明受到震撼写下这首诗。《雏妓》除了表达对幼女的同情,还试图以此事件为切入点,控诉男性把女性(而不仅仅是妓女)作为某种程度的性消费品,从而表达,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仍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未得到根本的尊重。
不过翟永明的观点很快受到了一位听众的挑战。这位听众表示,自己在法国生活过几年,觉得法国人是要给妓女争取更多权益,“就是说这种权益的捍卫并不是我不允许你做妓女,而是要改善你的工作环境,保证你的身体健康。但国内,包括您的诗里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消费的层面。”
翟永明则回应自己和这位听众谈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她说,自己当时写作的一个出发点,是因为身边一些男性朋友也认为妓女应该有自己的权益,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前提,即一切行为都应是自愿的,而很多中国的性工作者是被迫的。比如说,这名女孩只有12岁,显然不具备自主抉择所需要的判断力。“在中国,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时候去谈权益可能有点奢侈。如果雏妓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那300多个男人都要因此而被判强奸罪。” 翟永明说。在这种情况下谈尊重选择的自由,只能造成对女性更大的伤害。
女性必须以主角身份讲述自己的故事
学者李剑全程话锋犀利,她试图以富有激情的演说方式提醒人们,女性仍处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被压制着的女性仍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因而必须去反抗和斗争。她认为,女性的身份是被男性定义的。“女性跟阴柔联系在一起,男性跟阳刚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我们应该反思并且去反对的社会潜在的歧视性,这是男权贩售的一种观念。”男人用自己的形象定义了神,用自己的好恶定义了历史,用生殖器定义了性。这种情况下,女性只能处于被支配地位。
她认为“女性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一定要成为人生故事中的一个主角,而不是一个配角,甚至在舞台上没有角色的一个人物。”她谈到很多中国女性都不是为自己而活,似乎活着就是为了丈夫和孩子。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制约。而谈到具体应该如何做,李剑则呼吁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去创造新的事物。比如写作,在公众场合朗诵像《雏妓》这样的诗歌。但她也补充道,要求表达绝不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如果你的自由和诉求没有建立在对他人的自由和诉求同等关注和尊重的前提下,你的自尊就不可能成立,相反你只是自溺和自恋。”
用母性和爱去建构新的社会
不同于李剑所追求的不平静,主持人王歌强调以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去改造这个社会。她从西方学者列维纳斯的理论谈起,说到西方社会建构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倾向自我的我学(egology),出发点是个人自由。王歌试图从母亲的视角,提出一种母性逻辑。
她认为在这个消费社会,我们总是提前预设数值,认为一切都是可量化的。当我们考虑正义、公平的时候,我们总是和对象处在一个对等的关系中,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在这个预设下,所有的关注都变成了一种欲望的消费。但王歌以为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种虚构。“我在想,是不是存在一种母性的事物,它不是等价交换的。就像母亲对自己子女的给予行为是一种馈赠,不是为了养儿防老,也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因此王歌提倡以馈赠的逻辑来代替交换的逻辑。
就正义而言,她认为需要有补偿性正义来替代惩罚性正义。惩罚当然可以遏制一时之恶,却无法教导人向善。人们维护正义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惩前,甚至不是为了毖后,而应是为了善后。我们可以要求更多宽恕,以宽恕的逻辑来补充正义的逻辑。不过她也提到,我们必须对历史和当下的过错有足够的认知,像我们这个民族这样地健忘,不应是母性逻辑的题中之意。
此外,不同于李剑对政治的理解,王歌认可用爱的、情感的逻辑来代替支配的、权力的逻辑。她相信女性完全可以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为什么不能是友爱的呢。我们为了自由和平等相互斗争,划分左派和右派,为什么不能预支一点爱呢?没有哪个母亲对子女说,你得先爱我,我才爱你。母性是这样一种无条件的预支。”
而被认为贯穿人类历史始终的生产概念,在王歌这里也遭到了质疑。她认为生产本身就是一个很男性化的概念。人生应该是一个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过程。重要的不是我们生产了多少可见的产品,获得多少可量的成果。“我觉得人类最本真的东西,哪怕里面五味杂陈,有各种毛病,各种缺点,各种幽暗的东西,但它能一次一次激发我们,使我们成长为一个特别好玩的自己。”在王歌看来,这是最重要的。
链接
雏妓 (作者:翟永明)
雏妓又被称作漂亮宝贝
她穿着花边蕾丝小衣
大腿已是撩人
她的妈妈比她更美丽
她们象姐妹 “其中一个象羚羊”……
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宝贝
宝贝也喜欢对着镜头的感觉
我看见的雏妓却不是这样
她12岁 瘦小而且穿着肮脏
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
或者 根本已装不下哪怕一滴眼泪
她的爸爸是农民 年轻
但头发已花白
她的爸爸花了三个月
一步一步地去寻找他
失踪了的宝贝
雏妓的三个月
算起来快100多天
300多个男人
这可不是简单数
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那么多老的,丑的,脏的男人
要趴在她的肚子上
她也不明白这类事情本来的模样
只知道她的身体
变轻变空 被取走某些东西
雏妓又被认为美丽无脑
关于这些她一概不知
她只在夜里计算
她的算术本上有300多个
无名无姓 无地无址的形体
他们合起来称作消费者
那些数字象墓地里的古老符号
太阳出来以前 消失了
看报纸时我一直在想:
不能为这个写诗
不能把诗变成这样
不能把诗嚼得嘎嘣直响
不能把词敲成牙齿 去反复啃咬
那些病 那些手术
那些与12岁加在一起的统计数字
诗、绷带、照片、回忆
刮伤我的眼球
(这是视网膜的明暗交接地带)
一切全表明:都是无用的
都是无人关心的伤害
都是每一天的数据 它们
正在创造出某些人一生的悲哀
部份地 她只是一张新闻照片
12岁 与别的女孩站在一起
你看不出 她少一个卵巢
一般来说 那只是报道
每天 我们的眼睛收集成千上万的资讯
它们控制着消费者的欢愉
它们一掠而过 “它”也如此
信息量 热线 和国际视点
象巨大的麻布 抹去了一个人卑微的伤痛
我们这些人 看了也就看了
它被揉皱 塞进黑铁桶里
200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