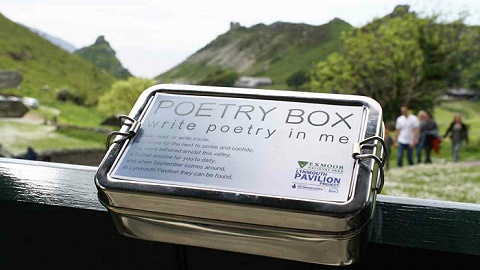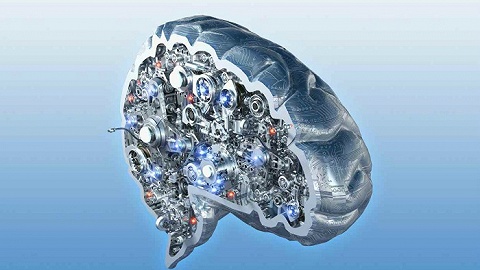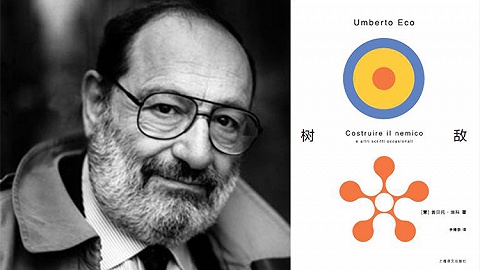编者按:仿佛转眼间,意大利作家、学者、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离世已近7个月。今年2月19日,84岁的埃科因癌症病逝。在欧美,知识分子间有一个隐蔽的观念在作怪:假如你不读翁贝托·埃科,你就不能算得上一个有知识和有趣味的人。想必中国读者对这位学富五车、博古晓今的欧洲作家也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玫瑰的名字》既已出版中文译本,其后的《傅科摆》《波多里诺》《密涅瓦火柴盒》也使中国读者得以见识这位“学霸型”作家渊博而繁杂的叙事和写作风格。
上海译文出版社将于今年出版埃科多部生前近作,其中就包括杂文集《树敌》。《树敌》全书收文15篇,内容跨越古今,将作家的多重身份融合于一本书中:我们既能看到学者埃科的哲学反思、文学惦念,又能看到公共知识分子埃科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有小说家埃科创作的蛛丝马迹,也有老顽童埃科以妙想奇思书写生活滋味。下面这篇文章摘选自该散文集的开篇之作《树敌》一文,埃科旁征博引,旨在探查人类史上“制造和定义敌人”的根源与过程。从黑人、吉普赛人、犹太人,到妓女、女巫、麻风病人,再到今天的欧洲移民,我们是如何将“差异性”定义为“威胁性”,继而将“与我们不同的人”定义为“敌人”的?道德是否有能力制造或维持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我们该如何面对差异呢——是加紧树敌,抑或尝试理解?
《树敌》
文 | 翁贝托·埃科
为什么需要敌人?
敌人是衡量我们自身价值的参照物
几年前,我曾在纽约遇到一个名字十分拗口的出租车司机,他说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随后,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意大利。他又问起意大利有多少人,当他得知意大利的人口竟如此之少,且官方语言并非英语时,显得十分震惊。
最后,他问我谁是意大利的敌人。我问“什么?”,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他想知道这几百年来意大利在和哪个民族打仗,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说我们没和任何民族打仗。他耐着性子,继续向我解释他想知道谁是我们的宿敌,也就是那些曾经和意大利人相互残杀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即使是在那场战争里,最初的敌人和最终的敌人也并非同一个民族。
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下车时,我为本民族这种麻木的和平主义多给了他两美金的小费。结果刚一下车,我就突然意识到刚才本应这样回答他: 意大利人并非没有敌人,但却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根本无法在“谁是敌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因为他们总是在内部持续地争斗: 比萨和里窝那斗,归尔甫党和吉伯林党斗,北方派和南方派斗,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游击队斗,黑手党和国家斗,政府和法院斗——只可惜当年还没发生两届普罗迪政府的倒台事件,否则我还可以向他好好解释一番什么叫在盟友的“火力支援”下打败仗。
不过细细想来,我的确认为我国最大的不幸恰恰就在于近六十年来,我们不曾有过真正的敌人。意大利的统一得益于奥地利人的存在,或者如白尔谢Giovanni Berchet (1783—1851),意大利浪漫派诗人、文艺理论家。所说,得益于“粗野且令人生厌的日耳曼人”;而墨索里尼则是通过一战时期“残缺的胜利”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语,指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却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利益。多加里战役和阿杜瓦战役之辱以及犹太式的富豪民主所强加于意大利的不公正裁决才成功激起了国民的复仇情绪。且看当伟大的敌人苏联解体,“邪恶帝国”逐渐消失之时,在美国出现了怎样的局面: 他们的救世主身份濒临崩溃,直到本·拉登出现时才得以缓解;后者对美苏对抗时期从美国所受之恩惠念念不忘,终于在这关键时刻向美国伸出怜悯之手,为布什政府提供了树立新敌,从而提升民族凝聚力及巩固自身权力的绝好机会。
拥有一个敌人不仅对确立自身身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一个对照物,用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体系,并通过与其对阵来突显自身的价值。因此,当这样的对立者不存在时,就需要人为地树立一个敌人。我们不妨看看维罗纳的光头党在此事上所表现出的“慷慨的灵活性”: 凡不属于本团体的任何其他团体都被看作是他们的敌人。所以说,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并非简单地“识别对自身具有威胁性的敌人”,而是制造和定义敌人的过程。

谁是敌人?
与我们不同的人,差异性是敌人的标志
在《反喀提林演说四篇》中,西塞罗本不需要对敌人的外表进行描述,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喀提林阴谋叛变的证据。然而,在进行第二次演说时,他却特意将喀提林盟友的嘴脸描绘了一番,将其卑劣形象影射到核心人物喀提林的身上。一群在夜宿宴会的家伙,与厚颜无耻的女人纠缠不清,沉迷于酒池肉林,头戴花环、涂脂抹粉,被女色折腾得萎靡不振,还口出狂言要屠杀忠诚的市民,将城市付之一炬……他们就在大家眼前: 头发一丝不乱,胡须修得整整齐齐,身着齐脚面的长袖衣衫,披着面纱,而不是裹着长袍……这些表面如此精致儒雅的“少年”不仅学会了唱歌跳舞、谈情说爱,还学会了捅刀子、下毒药。西塞罗有着与奥古斯丁相同的道德伦理观,都十分鄙视异教徒。因为他们与基督教徒不同,常常流连于马戏场、剧院和露天剧场,以及庆祝酒神节。由此看来,敌人是与我们不同的人,他们遵循有别于我们的习俗。
外族人就是一种典型的异类。早在古罗马时期的浮雕作品中,蛮族人就总是以一副胡子拉碴和塌鼻的形象出现。众所周知,就连“蛮族人”这个词本身都在影射外族人在语言及思维上的缺陷蛮族人一词的意大利语为“barbaro”。该词是一个拟声词,来自balbutire(意为结巴,口吃)。因此,该词原本用于形容那些说话含混不清的人。
然而自古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异类被我们当作敌人,并非由于他们构成了直接威胁,而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代表显示出某种威胁性——虽然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我们。这也就意味着不是威胁性突显了差异性,相反,是差异性成为了威胁性的标志。
黑人由于其独特的肤色而成为所有种族的异类。在一七九八年美国的第一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针对“黑人”一词的如下描述: 不同黑人的肤色也有细微的深浅差异;但他们的面部特征都无一例外地与其他人种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脸颊圆,颧骨高,额头微突,鼻子短、宽且扁,嘴唇厚,耳小,总之外貌丑陋奇异。黑人妇女的腹部下垂,臀部丰厚,身材类似于马鞍形。这个不幸的人种天生就带有如下恶习: 懒惰、不忠、记仇、残忍、无耻、狡诈、欺骗、下流、分裂、卑鄙、放荡,这些低劣的品行令他们无视自然法则,同时丝毫感受不到良心的谴责。他们不知同情为何物,是人类腐化堕落的可怕典型。黑人是丑陋的。敌人必须丑陋,因为只有好人才配拥有美丽(“身心至善”的观点)。美丽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在中世纪时被称为integratis拉丁语,完整、完善。的品质(即全方位具备代表某一种族平均素质的所有特征。因此,对于人类来说,肢体残缺、眼睛残缺、身高低于平均标准或呈现出“非人类”的肤色,这些情况都属于丑陋的范畴)。这样一来,对于像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和侏儒迷魅这样的人物,我们立刻就会把他们当成敌人的典型。
因为社会地位低下而被划入丑人行列的显然还包括流氓惯犯和妓女。不过说到妓女,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话题,一个关于性别敌视或性别歧视的话题。自古以来,一直是男性主导社会,书写历史,或一边主导社会一边书写历史,所以女性向来都被描绘成“祸水”。我们可不能被女人天使般的容貌所迷惑,相反,正是由于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都以温柔美丽的形象出现,民众更感兴趣的杂文世界一直在把女性的形象妖魔化,无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现代都是如此。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传播疫病者处以刑罚的根源。但金兹伯格所描述的迫害还不自觉地体现出另外一点: 麻风病人被与犹太人和撒拉逊人扯到了一块儿。许多年代史学家都曾有过类似的记述,说犹太人是麻风病人的帮凶,因此有许多犹太人也与麻风病人一起被烧死。“当时,无法无天的民众对麻风病人进行就地处决,在完全不通报神父或地方长官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他们关在房子里,连同牲口和家具一起统统烧掉。”

树敌是人类天性吗?
战争无可避免,只能加紧树敌
树敌还包括让敌人“自愿承认”的过程。许多戏剧和小说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类似于“丑小鸭”的形象: 由于遭到同伴们的鄙视,他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自己确如同伴所说的那般丑陋。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此看来,敌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文明在不断进步,敌人的形象也不能被消除。树敌是人类天性的一种需求,就算是性格温和、热爱和平的人也不能免俗。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是把敌人的形象从某些人转移到某些自然力量或具有威胁性且必须被战胜的社会因素上。例如: 资本主义的剥削、环境污染、第三世界国家的饥饿问题等。如果说上述树敌行为都“不无道理”,那么正如布莱希特所说,对于不公正现象的仇恨和报复便也会翻转脸面,变成正义。
既然树敌是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那么在此种需要面前,道德是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呢?我认为,道德的作用并不在于粉饰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在于试图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对波斯人的仇恨,因为他对波斯人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恺撒对于高卢人表现出高度的尊重,最多也只是让他们在每次投降时痛哭流涕一番。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相当赞赏,说他们体格健美,对于他们的指责也仅限于不讲卫生及怕苦怕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炎热和干渴。
尝试去理解对方意味着打破陈规,而不是否认或消除双方之间的差异。
然而,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此理解敌人,只有诗人、圣人或叛徒才能做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能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一九六八年,美国出版了一部作者不详的作品: 《来自铁山的秘密报告: 关于和平的可能性与渴望度》(甚至也有人把它记在加尔布雷斯的名下)。显然,这是一篇反战的文章,或者说是一篇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认为战争无法避免的文章。发动战争就必定要确立对抗的敌人,因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直接导致了确定及树立敌人的必然性。因此,这篇文章以极为严肃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整个美国社会转而趋向和平的态度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只有战争才是促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战争所带来的消耗是调节社会良性发展的阀门: 只有战争才能消耗社会的储备物资,战争是一只飞轮;有了战争,一个群体才会有“国家”意识;如果没有应对战争的经历,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只有战争才能维护不同阶级之间的平衡,才能妥善处置和利用反社会的因素。和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以及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战争则能以最正确的方式疏导各种骚动的社会力量,赋予他们某种“地位”。军队是穷苦之人及被社会边缘化人群的最后希望;只有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战争体系才能驱使社会付出血的代价来换取其他本不依靠战争的产业——如汽车产业——的发展。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战争是解决多余生命体的阀门;如果说直到十九世纪,在战争中死亡的多半还是有价值的社会群体(士兵),留下的却是老弱病残,那么如今的战争体系已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朝养老中心等地点进行定点轰炸。比起残杀幼儿的宗教仪式、禁欲行为、强制断肢及过度使用死刑等行为,战争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说到底,虽然战争充满了冲突和对抗,但却是一种最为“人性化”的发展艺术。
这么说来,我们应该坚持且加紧树敌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堪称典范的模式……不过,即使没有《一九八四》中描述的这般疯狂,我们也能意识到人类对于树敌的需要。我们正在见证自身对新移民群体有多害怕。我们把某些非主流的外族个体的特点扩展到整个民族,把罗马尼亚的移民树立成意大利的敌人。对于这个正在经历种族变革、对自我身份的识别感到困惑的社会,移民成了理想的替罪羊。
当然,最为悲观的观点出现在萨特的《禁闭》里。一方面,由于异类的存在,我们才能认清自己,基于这一点,才有了共存和忍让。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这个异类古怪到让我们无法忍受,由此,我们便把他放到敌人的位置上,也就构筑起了我们的人间地狱。当萨特把三个生前互不相识的死人置于同一间酒店房间里时,他们中的一个参透了其中可怕的真相:
你们会明白这道理是多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儿没有肉刑,对吧?可我们是在地狱里呀。别的人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我们得永远在一起……这儿少一个人,少一个刽子手……他们是为了少雇几个人。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

本文节选自《树敌》一书(翁贝托·埃科 著,李婧敬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9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系编者所加。